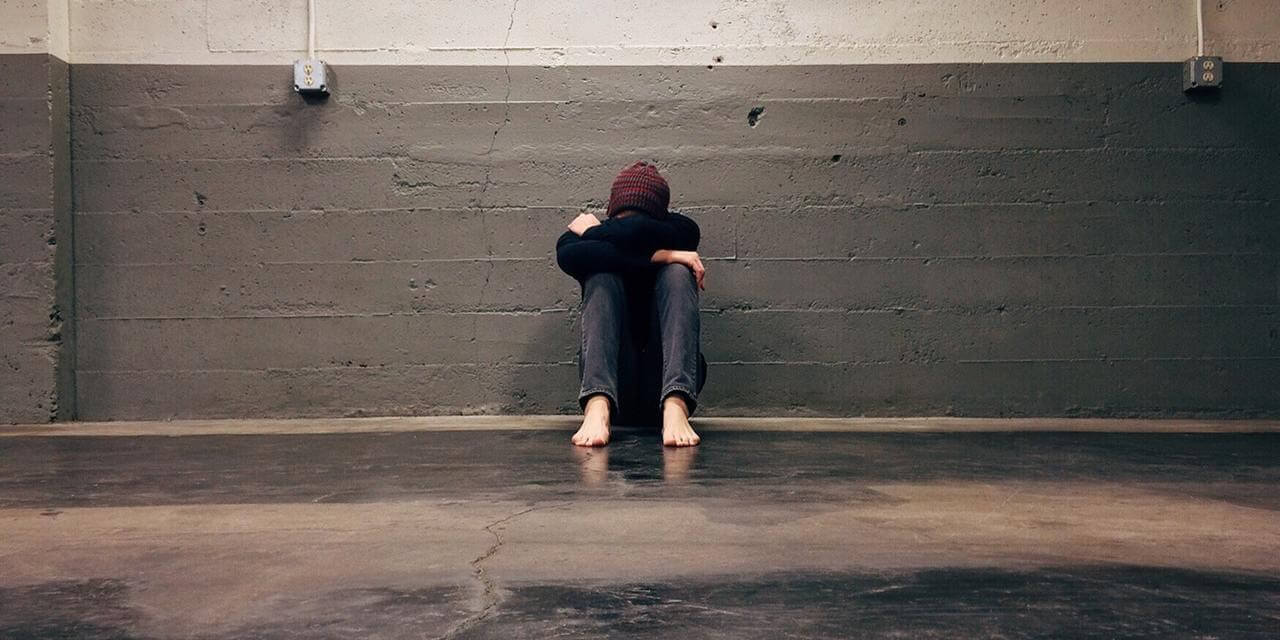文/璃人泪
“学霸”父母养育了“学渣”孩子,并不是个别人的烦恼,其原因因人而异。在吐槽体制、反思自我、恨铁不成钢之外,友人现身说法:她家的孩子的不专注是一种病!“感统失调”这一名词的提出不过半个世纪,相关的门诊和以此为卖点的培训机构却层出不穷。父母们对付不了的“学渣”是不是得病了?

抱有此等困惑的读者,一定能在《文明中的疯癫: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一书中得到镜鉴。作者安德鲁·斯卡尔是社会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学者,而历史上,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正是在文化与科学之间摇摆不定、莫衷一是,用跨学科的视野来看或许更全面。关于精神疾病,今人时常怀有和古人一样的困惑,甚至在许多细节上,今天的社会学者和科学家也没能完全弄明白。因此,了解前人看待精神疾病的历史,是一段略带神秘、新奇有趣、亲切生动的旅程。
在混杂着神话与传说的古代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向神明求解释,将疯癫诉诸某种超自然力量。如同各个民族的先民构筑各自的起源神话,在当时的认知下,神明的解释有某种镇定之效——相比于随机产生的疯癫,有迹可循能令其不那么可怕,尽管“伪科学”的解释本身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
早期医学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改变。虽说盛行许久的体液说已不足为据,至少替医者打开了一条思路:疾病的根由存乎人体,精神疾病概莫能外。但是精神疾病又是极难解释的,在不同患者身上症结不同、表现各异,治疗方法更是无奇不有,其疗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医者的一厢情愿。
书中列举的种种治疗方法中,一度大行其道且广为人知的可能是额叶切断术,我们知晓它的途径却可能来自绘画、文学、电影等场景中的可怕印象。这号称简单、迅速的手术,是将一支冰锥刺入眼眶,着实触目惊心。此外,注射毒物、刻意制造脑膜炎、降低体温至29度以下等旁门左道,更是时常令患者有性命之虞。
采用何种治疗方式有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譬如,在15世纪的荷兰出现了第一家疯人院,仅可容纳十人。这一模式大受病患家属的好评,因其大大减轻了照顾病人的负担,很快供不应求。而在17世纪的英国,精神疾病就不见得是负担了,一位医生自豪地名之以“英国病”,称它常在显贵阶层流行,是一种神经纤弱的文明病,理应被善待。到了20世纪,受到战争创伤的士兵可没那么好运,精神科医生与军队里的上司立场一致,认为所谓的“炸弹休克”受害者根本就是逃兵和胆小鬼,应当用酷刑去刺激他们——巨大的痛苦逼迫“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瘸子走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医学发展突飞猛进,在精神病学领域也有了看上去客观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医生们可以按图索骥,无需主观判断有病没病,临床处方也如出一辙。余下的事情,是否应当交给科学家去研究更多关于大脑的奥秘、完善目录、研发新药呢?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环境的影响。因为“疯癫的根源隐藏在生理与社会那不可捉摸的混合体之中”,浸淫其中的大多数接受了今日的规则,未觉有异。譬如斯卡尔感慨,在用DSM标准化诊断的当下,我们也失去了昔日精神分析学家倾听和了解个体的耐心,而后者不是全然无意义的。又或者,当我们将日常生活的困扰交给精神药物,归咎于心理疾病时,我们也交出了一部分对自我的掌控。进而,我们再给掌控不了的孩子贴上有病的标签。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就关注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的孩子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美国,平均每五个男孩里就有一个)。让三岁的孩子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现实令人不安,和斯卡尔一样,高普尼克也认为,除了生理性的因素,我们应当着眼于社会性因素,视孩子的大脑发育状况,为他们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科学的发展,本是为人服务的,倘为了简化问题而忽视身体的真实需求,未免本末倒置了。疯癫的历史刚好为清醒者镜鉴,一纸药方不能取代对自我、对他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