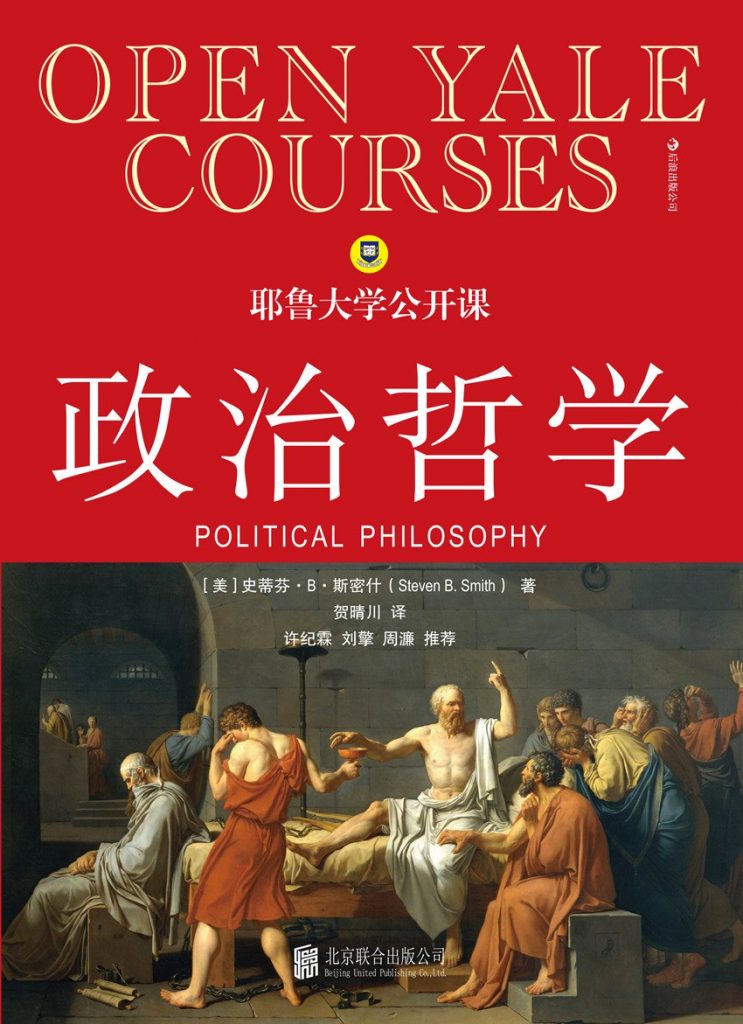
正义和自由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字眼却是最含糊不清的普世价值,我们可能对此类“永恒真理”都有着认同感,只是我们的认同是建立于形形色色的正义和自由之上。所谓普世价值应该是普遍适用、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如同永恒正义所包含的道德的局限与片面性意义,伦理精神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无法兼顾。在政治哲学中,这两者的冲突与矛盾更为明显,对此可以反观我们围绕着这门学问提出的问题,诸如政制是怎么产生的?政治家需要有怎样的技能?存在最佳政制吗?民众具有怎样的特点?这些问题归根究底是在考察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辐射出我们在追求公共善好和私人善好之间作出的妥协,最终来到“人的本性是什么”这一本源性问题。政治哲学的有趣和复杂都在于此,各个流派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只是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同主张。
对于国家而言,正义由公序良俗和法律制度共同构成,核心指向社会分配,这样便有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问题:制度是否能代表公平与公正?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马基雅维利认为善好中如果没有几分残忍是无法立足的,统治家必须有杀伐决断的勇气,因为在他眼里违背日常道德规范的极端状况才是状态,这种情况下,不能说他不追求正义,也许更准确地是,专制强权下的正义,这样的正义把希望都寄托在了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和秉性上。在此观点上,霍布斯加上了法律的框架,主权者决定的法律就是正义的,主权者受到法律的约束,然而,霍布斯又将公正的法律和良法做了区分,这似乎又有些矛盾,正义的法律未必都是好的。与霍布斯将和平置于最高目标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洛克认为主权者更应该做的是让个体自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好的,他的一大核心观点就是将个人财产分配引入到正义的概念中,从洛克这里我们看到商业国家的前景和资本主义的雏形。
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个基础设定的不同,罗尔斯得出了一个与洛克截然相反的答案,洛克认为机会平等,因而个人的劳动产物不能被干预,而罗尔斯的观点在于个人的天赋和才能本身就不是真正的起点,是社会赋予个体的一部分,需要为了共同利益再分配,在他看来,“法律是在稀缺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对公正的考量”,但这不禁让人怀疑,对善好的重新分配真的能带来社会平等吗?对此我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集体所有将导致集体漠视,正义的善好也不得见。相比起专制,表达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制似乎更正义,但它同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如果制度有了倾向性,又何来的正义?托克维尔表达出了民主暴政的忧虑,然而他也没有做出解答。正义究竟是什么?它无法脱离集体单独存在,这让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不公正的因素,上下求索,我还是回到柏拉图的命题,正义是与知识合作的权力,如果正义就是强者或强势阶级的利益,那我们只能期待占据优势者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然而谈论及此,不免又得谈论政制的结构,就此打住。
自由又是另一个复杂的命题,有趣的地方在于权利的让渡,以及自然状态下的我们是什么样的。霍布斯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在法律沉默之处享有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自由不是法律能干涉到的领域,这个观点应和了霍布斯的性恶论,人在自然状态下恐惧不安,冲突是常态,如果个人保留了任意做想做的事的权利,将不得不处于战争状态,强有力的专制统治就是克制人的自然欲望,因而自由不是法律能约束到的权利。与此相对的,也是我颇为赞同的是卢梭的观点,自由始于法律,这与亚里士多德理解的自由不谋而合,“自由并不只是意味着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而是必须赋予它一种道德约束,赋予它一种不是什么事情都能被允许的意识”。卢梭认为人生来是具有同情心的,只是进入社会以后变得理性、变恶了,因此法律约束从另一种程度来说是让人回归到他们本来的状态,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卢梭的另一个自由主义观念是社会契约将每个结合者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整体了,这时公意是一种普遍意志,我们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自己,然而这种转让很抽象,怎样才能达成这种公意呢?有德性的自由也许是我们能追求的最大的私人善好了。
最后想说与正义看似若即若离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理想国》的各种正义观中,有一种观点将正义与荣誉感、忠诚感联系起来,正义就是对一个团体乃至国家的忠诚,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美好的情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我们真正关心的东西仅仅是自己的东西,我们亲近它,因而更容易产生共情,而这种道德标准并非一定局限于国家,它仍然建立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法律制度上,如果这种公平在国家层面上排他,那将会演变为固步自封的沙文主义,蒙蔽了我们的心智,对移民的排斥就是爱国主义的畸形演变。“心有分寸”是我看到的对爱过主义最好的形容,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自发的情感,又能将这种生活形态化为自己的意志,它是开放的、高尚的、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只是如今爱国主义渐渐变成了一样过时的东西,愤世嫉俗成了一种保护色,人们好似活成了世界公民,批判也掩盖不了底下的冷漠。政治哲学离日常生活并不遥远,它需要我们从公共生活转向私人生活,审视自己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