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璃人泪
忧郁是种病吗?倘说它是病,为何那些带有忧郁气质的名人有着难以名状的魅力?为何伟大的艺术家在忧郁中获得灵感?为何在特定的时期人们竞相以忧郁为荣?倘说它不是病,为何古往今来研究它最甚的是医生?为何它给患者及家属带来身心的折磨?为何某些药物似乎能缓解症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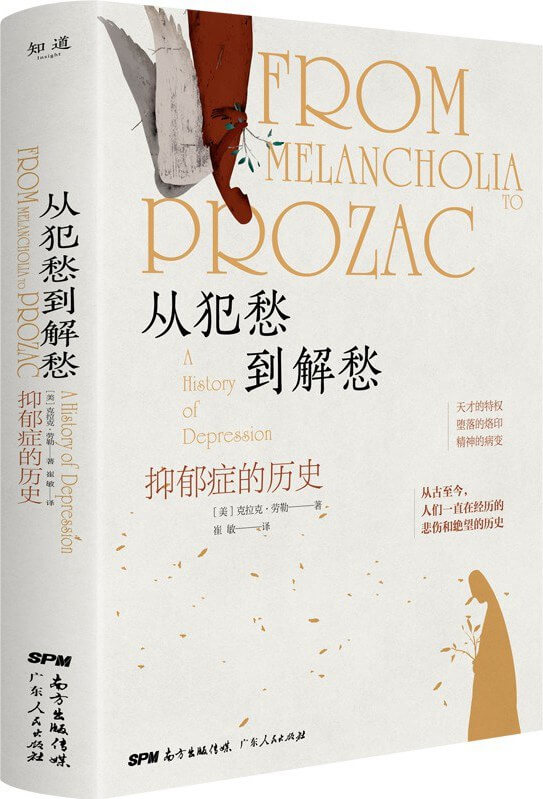
我们彷徨无措,不知何以解忧。美国作家克拉克·劳勒追本溯源,或能令人看得真切。《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讲述了不同时代人们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主人公:古罗马的盖伦、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们、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博学多识的《英语大辞典》作者塞缪尔·约翰逊、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劳勒带我们用已知的片段串联起未知的领域,即便介绍医学研究的专业知识,读来也绝不“忧郁”。纵观历史,无论人们对忧郁《或抑郁)的认知如何,都在探索“解忧”之道。
有些方法如今看来荒诞无稽,对照当时人们对病因的归纳却也是“对症下药”。譬如,根据古希腊人的“体液说”,被他们成为“忧郁症”的疾病肇因于体内黑胆汁过多。那么解决方法便是清除黑胆汁,无论是放血、水蛭疗法还是服用有毒的嚏根草催吐催泻都是达成目的的手段。18世纪的英国医生乔治·切恩算是那个年代的“网红”,他很擅长跟不懂医学的人交流,自称治好了自己的抑郁,也是他美其名曰“英国病”,将症结归咎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导致的贪婪和神经纤弱,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患病。切恩强调,吃素戒酒、调理肠胃,辅之以体育锻炼,是治疗“英国病”的良方,这些不成其为治疗方法的方法令其声名大噪。抑郁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有社会性原因,19世纪的精神疗法颇具人文色彩,友善陪伴患者、倾听并劝慰,或是人之本能。但劝说未必总是有效,分析抑郁患者的精神世界逐渐成为一件专业的事。
今天我们如何治疗抑郁症?无论身边有没有患者,大多数人都能像报出感冒药、腹泻药的名称一样,熟稔地报出“百忧解”,这实在是制药公司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百忧解和抗抑郁药的普及是上世纪末的事。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手册》第三版问世,“成为新型抑郁症的《圣经》”,不同医生按图索骥,也可根据症状给出相同的诊断,那么开出相同的药方亦顺理成章。而相比于前人放血、电击、额叶切除之类的激进疗法,吃药更易被接受,听起来也更有现代科学的依据。于是,抗抑郁药物销量攀升,似乎是对抗情绪问题的解药。
对此,早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一方面,《手册》中的评估标准不算完善,一个正常人遭遇重大变故或严苛压力时,也极可能产生《手册》中的症状,未必需要立即纠正。另一方面,药物的效果也饱受质疑,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们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遑论药物被滥用的风险。归根到底,我们对抑郁症的了解依然很肤浅,甚至充满主观色彩。
生活在不同时代,人们面临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产生抑郁虽有身体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因素,后者可能不易被其他群体承认。拿今日常见的产后抑郁来说,父辈们初为父母时,难道不曾有过艰难岁月吗?他们很难理解物质条件更优渥的当代父母如何身心脆弱,但这显然不能单纯以心理素质作结。解忧应当双管齐下,对效率的追逐让我们倾向于简化问题、交给药物,染液当驻足倾听旁人的声音,予以共情和关怀。尝试化解个人的忧郁,亦是在为抚平社会的忧伤贡献涓滴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