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时候不大喜欢诗歌,或者说,略带点不以为然。
那个时候,我认为,真正的文学是小说。诗歌算什么啊,就那么几个字,随便发点感慨,要么就是悲秋伤古的,别那么矫情好吗?最早我们学习的唐诗有个门类叫“山水田园诗”,我一直特好奇,那个时候的那些山中景色有那么美吗?这些诗人为什么没事干总要抒发点对美景的感叹呢?
啊,孩子啊!以后岁月漫长,我自是经历了不屑诗、不读诗到读诗、为诗战栗。到如今,不是岁月的终点,但是已然已经敬畏诗歌了。当我开始爱上读诗,曾经也为自己年少狷狂的态度羞赧,但是如今,我已经能接受在那个岁月里我不读诗不懂诗却洋洋自得,也坦然自己现如今对诗歌的敬畏感。
因为,你心里的九曲十八弯,有关岁月关乎你对人生、宇宙的理解,诗歌里都有。
此去经年,上一次读葛晓音老师的《山水有清音》,还是不大能接受王维,说真心话,隔过时空,我依然觉得他矫情。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读黄晓丹老师的《诗人十四个》,竟然读到了王维的好,竟然爱上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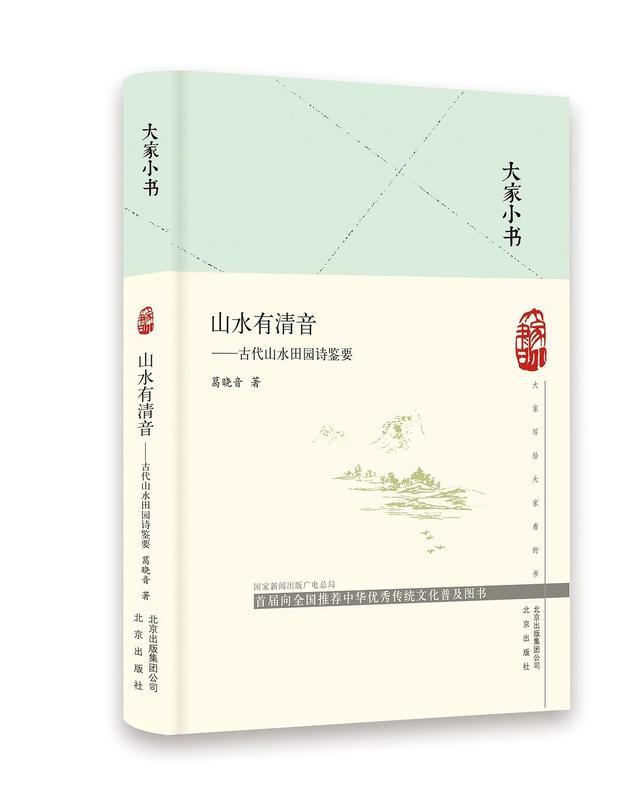
我不能说,黄晓丹的解读就要优于葛晓音,而是,到了某一个节点上,你恰恰是已经可以理解和接受“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而在这个节点上,就可以因为一言一词而走进与诗人共鸣的诗歌世界,以往,晓音老师再怎么鼓与呼,用灵魂之力来解读这些震撼灵魂的诗句的时候,就像叫喊于生人之间,而作为生人的你,并无反应。这并不能说是作为诗人和解读者的悲哀,亦不可归为读者的悲哀。你们虽然在同一个世界,但是其实又不再同一个世界,而每个人都可以安之若素,直到一个点上,你的灵魂冲破了时空的羁绊,或许能够被感动到的,也不是诗人千百年前写下诗句的本意,但是那有有什么关系。这些诗句,在时空和岁月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如果说人和人心灵的碰撞,灵魂的共舞是可遇不可求,至善至美的,那诗歌的字句就是挥舞在是空中的精灵,是指引你来到心灵的天堂的天使,它们本身,可以不具备任何意义,但是又拥有一切意义。
这种感觉是很玄妙的,但是又是非文字可以诠释的。

在2019年代年末,我在黄晓丹老师的书里体会到了。这种巧妙的共振,不仅仅发生在读者与作者,也发生在读者与作者所选取的诗作作者间。因为如果没有这位作为解读者的中间人,你和王维、李商隐、陶渊明、辛弃疾、李白等十四个诗人之间还缺少一个共存的空间,你可能因为偏见——比如我年少时对“山水田园诗”的偏见和无意识,根本就不会选择去读去感悟诗歌中的世界,但是当你们都共存在这些文字的一个场里时,竟然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正好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在读“大家小书”系列的《陶渊明批评》,萧望卿老先生对渊明诗四言颇为不满,认为他的四言只是在在仿古,多是在模仿《诗经》和屈原,但是独独对《停云》颇为推崇,正好读到黄晓丹在“陶渊明与辛弃疾”里解读《停云》,可见真正好的文学,读者是心有戚戚焉。晓丹老师说,四言除去了大部分修饰的可能,独有一种警醒的力量。萧望卿先生也说,四言这种诗作题材可以发挥的并不多——就想到了我年少时候,以文字的多寡来判断文学的价值,也是real天真了。越是文字少有框架的格式,其实越是不好发挥的,再加上什么韵律的限制,必是朗朗上口,必是妙口生花,必是可与曲调相和;必是符合韵脚……诗真的是难写,但是在有限的四言、五言和七言里,竟然有所有的人生智慧和宇宙哲学,想一想,诗真的是神奇而恢弘的存在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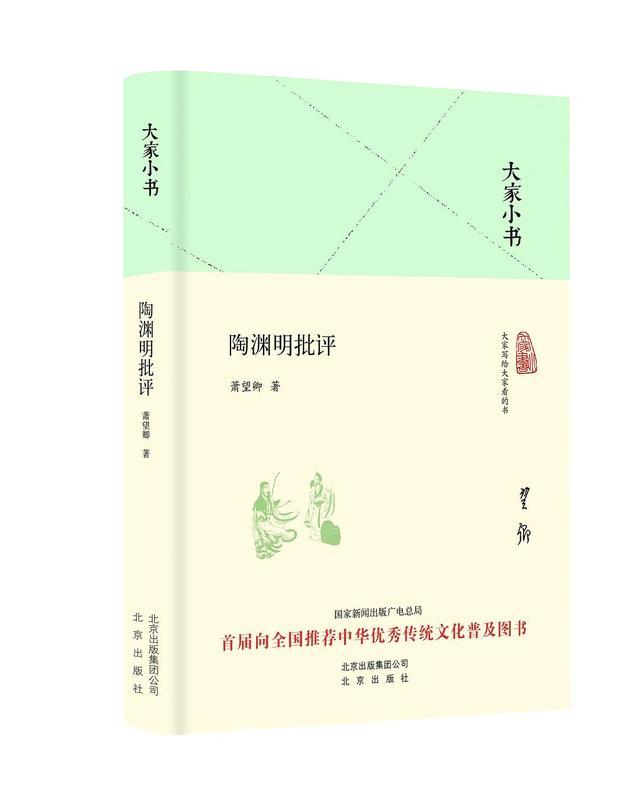
叶嘉莹老师曾经说,我遭遇到很多人生中的挫折、苦难、不幸的事情,我都是用李商隐的诗来化解的。这让我想到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据说她在绝望的时候,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籍,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帮助她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和生命的灯塔。在没有读过李商隐诗歌和冯友兰哲学的他人而言,这几乎是无法理解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渐渐地明白,书中有一切,一本书、一首诗,的确能拥有治愈人心、重塑自我的力量,然而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或者说,只有幸运的人才能在书中找到宇宙中最强有力的支撑。和就和这本书的起源又暗合了。黄晓丹老师这本书最初是和心理学相结合的讲稿,他想通过古诗来达到“自由联想”,在这种情感共鸣中释放、疗愈(读者与解读者)。
事实上,这相当有难度,可能很多有需求的人进入不了古诗的共鸣殿堂,而进入殿堂的人很多事内坚强的人——比如叶嘉莹教授,他们更期待美的享受而不是疗愈。不过不管怎么样吧,这样的学科碰撞很有趣,它像是多菱镜,一首诗给了你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当我们最终开始读诗并且读懂诗的时候,已经不再需要治愈了——千百年来人类都是这样过来的,“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那又如何呢?我们无需和古人相识,但是在时空中,我们都可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晓丹老师在书里说:现代人处理自己人生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有时我觉得文学阅读也能起类似的作用。诗人用作品呈现自身的困境和绝望,同时也将他们抵御绝望的能力贯注在诗歌中。当我们在文学中穿行,体验这些非常尖锐的痛苦时,又无时无刻不被富有人情味的智者所牵引,所陪伴。等我们走出诗歌,过往生命中的伤痛好像也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疗愈。
